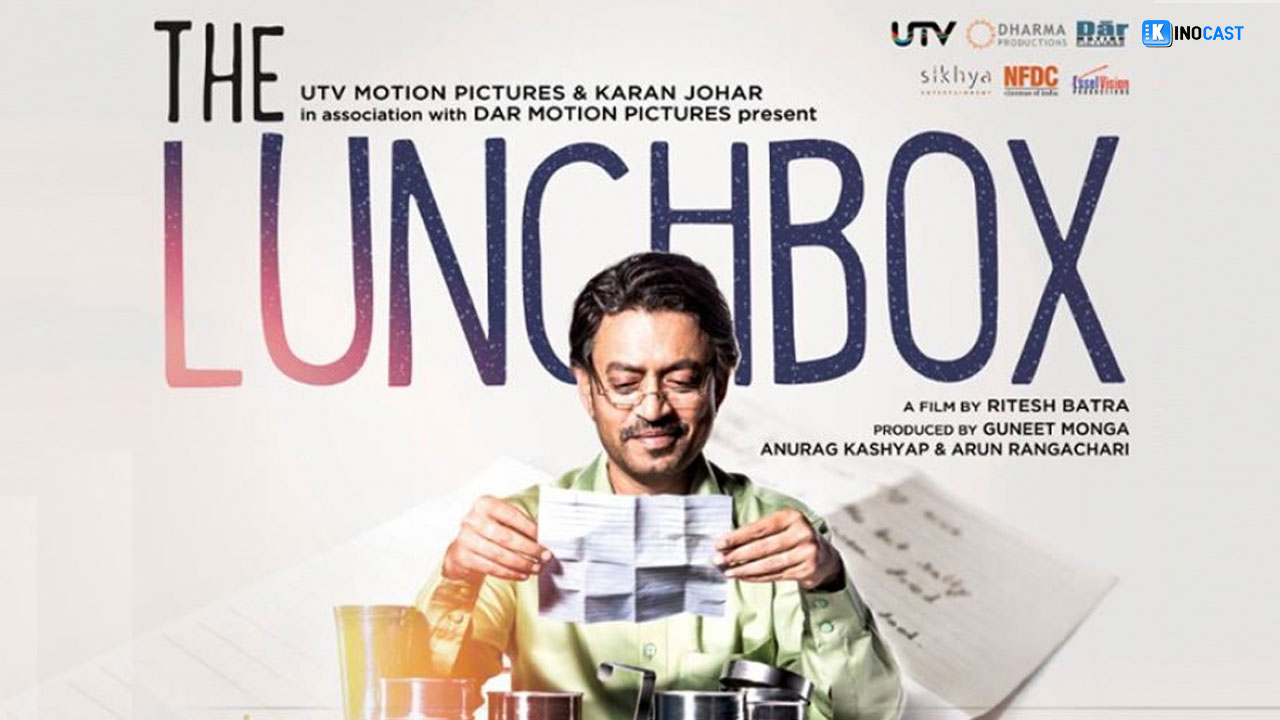澳門繁忙的八號A巴士,總算在閒日午飯過後擠出點空間。
「而家喺粉嶺搭去觀塘又係十幾蚊,搭去荃灣又係十幾蚊,鬼死咁貴。」阿全看着窗外的景色,和身旁的朋友談起現居地的變化。「澳門搭車始終抵過香港。」可能是唯一的不變之處,有點理所當然,說了好像沒說般。
阿全又看看車上的乘客,似乎不是這小島最勿忙的上班族和學生,也不是來淘空澳門的遊客。他覺得,眼前光景和回憶中的澳門,還未至於面目全非。可是,這樣的想法,又令他自己覺得自己有問題 — 咁都唔算變得犀利?
到了提督馬路站,巴士上的人開始多起來。在上上落落的面孔中,阿全看見這多年不見,還是一眼認得的舊相識,獨自一人坐在單邊位上。
喂,阿全向他叫了一聲。
啊,是你,我認得。阿貴定過神來,回道。
係呀,好耐冇見,二人同聲說。
你退休未?阿全問。
就快喇,做多兩年先啦不過,唔做嘢硬係周身唔聚財。不過而家想做都未必有得做就真,阿貴答。你退休未?阿全反問。
退咗喇,一二年退嘅,而家間唔中就過吓嚟玩幾日囉,搭程船,好快,阿全答。又道,我想做都冇得做啦,不過啲仔女都大晒囉。
阿貴無聲的點頭。阿全見沒有回覆,轉身向後望,才知阿貴應了。
阿全又說,八八年走咗之後,喺香港攞咗身份證,又揸澳門身份證,重幫啲仔女攞埋澳門身份證,兩邊福利都攞。
阿貴說,好呀,有錢派,兩邊都有得攞,又多福利。
巴士到了沙嘉都喇街。車上有個學生大聲在電話上數落老師,拉高巴士上的聲浪。
阿全說,澳門都變晒囉可。
阿貴答,變咗好多,唔同晒囉。
阿全說,以前做廠嗰陣,你咪跟阿邊個嘅。
阿貴答,係呀,死咗喇,佢重大我十年。
阿全問,咩事死。
阿貴答,生Cancer。
阿全回,都係冇病冇痛好呀可。
阿貴答,係。
阿全問,你今年幾歲。
阿貴答,六十二,你呢。
阿全答,大你三年,六十五。
阿貴答,哦,差唔多。
阿全說,咁你有冇搵呀邊個,以前同呀邊個一組嘅。
阿貴答,我知你講邊個,不過我唔係同佢哋一組,唔係好熟,不過聽講生意都叫唔錯。
阿全說,你記唔記得呀邊個,同咁上下過咗去香港嗰個呢。我同佢間唔時去拱北嗰邊飲茶,俾我哋撞到佢。
阿貴答,係呀,佢好似返咗珠海嗰頭住,買咗棟樓,都好好景。
阿全說,咁就好喇,最緊要有得住有得食,以前做到隻積咁都係為咗咁啫。
阿貴點頭。阿全沒有聽見回覆,但知道阿貴其實回過了。
望着一直繁榮的水坑尾街,阿貴說,而家啲嘢貴咗好多,特別係新馬路嗰頭,鬼死咁多人,都唔係我哋去嘅。而今喺高士德嗰頭多。
阿全點頭。他有點想說說香港的情況,但難得阿貴開口,有點想順着他閒談,講講澳門。和澳門故友談澳門,該是在澳門做的一件好事。
新葡京站上了一批遊客。
阿全笑問,重有冇去玩?
阿貴也笑,說,冇喇,我哋做呢啲,以前最鐘意玩兩鋪,一經過又玩,廠冇嘢做就去,都唔知輸幾多畀佢哋。又問,你呢。
阿全說,哈哈,咁忍得手。而家都係玩一兩鋪咁啦,過吓手癮,唔會輸身家。
阿貴說,以前阿邊個咪係囉,玩晒成個月糧都有,真係。
阿全問,係喎,咁阿邊個而家點。
阿貴答,都冇聽到阿邊個點喎,都失晒聯絡,若果唔係好似我哋咁撞到,都冇機會見,傾下偈囉。
阿全笑答,係囉,真係好呀撞到你。
阿全又問,你喺邊落車?
阿貴答,新馬路呀,你呢?
阿全答,我哋都係喎,點都要去吓嘅,去睇吓又變成點囉。
阿貴又只是點了一下頭。這次阿貴和阿全都站了起來,看得見他點頭了。
阿全說,咁你去新馬路做乜?
阿貴說,約咗朋友。
阿全說,啊,好呀。
巴士經過新馬路站,但沒有停車,繼續向前行。
哎呀,做乜唔停㗎。阿貴說。
係囉,點解唔停㗎,過咗喎個站。阿全說。
阿貴笑了,說,掛住講嘢,唔記得襟制㖭。
阿全也笑,說,係囉,我又以為你襟咗。
阿貴說,哈哈,我又以為你襟咗。大家指意大家。
阿全說,哈哈,咪就係,真係。不過,我又以為新馬路一定有人落。
阿貴說,係囉,新馬路通常一定有人落車㗎嘛,今次竟然冇。
阿貴阿全都笑而不語。
阿全問,下一個站喺邊。
阿貴說,要去到十六浦喇。
阿全笑了,說,使唔使賭番兩鋪。
阿貴也笑,最尾都係載我哋喺呢度落,可以去玩喇。
阿貴阿全都笑而不語。
阿全說,既然係咁,我同朋友喺十六浦行吓。
阿貴說,都好,行吓囉。
巴士到達十六浦。華麗的索菲特大酒店,好像不能穿越的舞臺佈景。
阿貴說,再見。
阿全說,再見,再見。
二人往相反方向走,頭也不回。
在十六浦下車的,還有一位也指意阿全阿貴會在新馬路按制下車,所以也沒有按制,然後一起錯乘至十六浦的香港遊人。